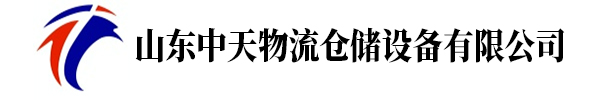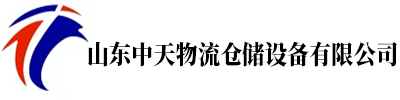湘潭传统龙舟赛
来源:环球国际平台网站 发布时间:2025-08-11 01:20:31
关于湘潭龙舟前史的来源,晚清文学家王闿运在其主编的《湘潭县志》中记载:一条龙舟在竞渡时遇到大风波,船翻后沉入壶山下的陶公潭,船上的人们则被巨大的漩涡带到深潭下的龙宫。龙王见问:“为何落水入宫?”船夫们答复说:“参与龙舟竞渡,为家乡父老求得风调雨顺,人兴财旺。”龙王被这一答复感动,特许他们在龙宫玩耍七日,再护送回岸。上岸后,人们把这条船的龙头摘下来,以示留念。从此今后,每年湘潭划龙舟,总会有一条船没有龙头。
乾隆年间《湘潭前史考述》中的一首竹枝词也记载了这一个故事:“龙船驿外赛端阳,认得船头是阿郎。底事失头龙惊讶,黄龙久不下观湘。”末后还附加了一小段文字阐明,说是“湘潭驿在观湘门彼岸。龙船竞渡,传吾邑有二船沉龙宫,宝糕孔留七日归。今陶公船号‘失头子’,尚可划;黄龙船不行复划,唯陆地金装迎送锦标”。不过这儿说到的沉入龙宫的船是两条:陶公山(即壶山)具有的“陶公号”,下水而无头;黄龙巷具有的“黄龙号”虽有头但不能下水,便在陆地上盛装“接标”。
这些关于湘潭龙舟来源的传说故事已不行考,但湘潭龙舟竞渡的风俗,却一代代地传递着。
湘潭接近湘江,壶山脚下,湘江、涓水、涟水会聚构成一个天然港湾。明清以来,因其上连两广、下通洞庭湖入长江的地理位置,成为南边重要的货品集散码头,曾有二十余省在此设有商会,故有“天下榜首壮县”“小南京”“金湘潭”等美名。
其实早在宋代,湘潭沿江便建有街市,连绵十余里;明初,街区即沿湘江从东到西划分为十八个“总”。“总”这个特别的称号,来源于古代打更巡夜所设的“总铺”。跟着清朝湘潭商贸与城市活意向郊外会集,一总至八总的称号不会再运用,但郊外九总到十八总的地名一向连续到现在。
湘潭龙舟竞赛中,各个部队间的竞渡称为“斗标”;而在预备期间,每个龙舟队的代表都要到其他码头访问相约赛事。到时,船上的“标师”会大声“赞标”,岸上的码头则会派人“接标”,就在这一来一往叙往日友谊并确认当年赛事。
民间撒播的一些“标词”生动地流露出一些码头龙舟称号和挑战者的心态。例如十六总的龙舟队来到老街后,大声说道:“小小杨梅洲(船),脚踏下五都(船),要吃金凤肉(船),筷子一把收(船)。”十八总的人则回道:“脚踏双通(船),口含七星(船),身座朝龙(船),一扫和平(船)”,来轻视对方的龙舟。
不过,“标词”内容仍是以友爱的内容居多:“兄弟码头来助威,友谊榜首不能忘。湘江赛舟显身手,咱们永远是朋友。一往无前祝安全,码头上下喜洋洋。待到五月端阳节,举酒高歌凯旋还。”谈锋拔尖的标师常能化干戈为玉帛,使对手变为老友。
阴历三月三往后,十八总码头下的江面变得宽阔起来,又到了湘江涨水的时节了,老街一年一度的龙舟活动也拉开了前奏。
酷爱龙舟活动的陈建文曾经当过“国标龙舟队”的教练,带队到岳阳汨罗江参与过世界龙舟竞赛并获得不错的成果,退休后一向想打造一艘归于十六总中山码头的传统龙舟。在他的牵头下,由老铁匠林少奇、水手指挥沈成林等人组成了新的“中山龙舟委员会”。
据湘潭有名的龙舟活动爱好者林少奇介绍,龙舟宗族巨大:有10人划的“短龙”,有上百人划的“长龙”,有世界赛事上看到的“规范龙”,也有端午民间竞渡的“传统龙”。一条龙舟从组成结构、选材到保存都是十分考究的。规范的龙舟一般长25米,最宽处2米多,舟体主梁是用粗大的圆木做成的龙脊,贯穿整条龙舟,舟体中部用两个圆木穿插构成竖立的“油叉”,是拉紧前后船头的绞紧部件。载人后能调整舟体的弯曲度,确保承载50人不变形。
龙舟共分六个区:龙首用来扒开船头急流的河水为其开道,当地人叫“鹅峰”;接下来的“代桡”首要坐划手领头人;中心的“油叉”为鼓锣区;“油叉”前后是水手们集合的前后“鼓仓”,一般有16到20个仓位,左右均匀散布;尾部为“道浆”区,由两个长5米的洪流桨组成,需六人一起操作,用来为龙舟加快导航;除此以外还有正副指挥,两个锣鼓和机动水手,算计50余人。
造这样一条龙舟要用7个多立方米木材,200多公斤桐油,舟体自重2吨。如此巨大的龙舟在湖南甚至全国也很少见到。除此之外,龙舟在竞渡时还会装上龙头和龙尾,一条龙舟的气势很大一部分取决于龙头。林少奇说,龙头大多用整木雕成,涂成赤色,称“红龙”,也有涂成黑色和灰色的,并在成型后,安上鼻球、龙须、龙舌等,使龙头夺目有神,整条龙舟也神气活现。
周赞坤是十八总最有号召力的白叟之一,眼看着分出去的十六总中山龙舟队一年年强大,周赞坤打电话约老友陈绍林到茶馆来商谈龙舟工作。陈绍林年轻时是湘潭有名的划船高手,终年漂在河里,不同时节、各个地段的水流状况他都一览无余;又因为年轻时读过一些老书,谈锋拔尖,所以仍是当地有名的“铁嘴标师”。在人们的一起努力下,十八总龙舟通过精心修补面目一新。
阴历五月初一,发动龙舟游街时,老街被看热烈的人围了个风雨不透。龙舟在世人的簇拥下慢慢起程,由摩托、腰鼓和西乐队组成的部队从老街动身,通过一大桥进入市中心。路上行人和车流停下来给龙舟让路,可见龙舟文明在当地人心中的重量,当然这也是十八总龙舟爱好者最幸福和荣耀的时刻。
龙舟抬到江边后,便是盛大的下水祭奠仪式了。周赞坤一声令下:杀猪宰羊、抛撒五谷,宣读龙舟祭文、点画龙眼、烧香请求风调雨顺……最终,当一只鸭子被标志性地杀上一刀、抛向河面、消失在滚滚江水中时,周赞坤脸上露出了一点笑脸,陈绍林在一旁打气说:本年的竞赛会一往无前、马到成功—这或许便是祭奠仪式带给人们的期盼与安慰吧。
定下竞赛部队后,龙舟在周陈两人的带领下,快速划到杨梅洲岛上“抢柳”,将一把新长的绿柳摘下插到“油叉”上。岸上观众看见船上飘动的绿柳,感觉龙舟在奔驰。
2011年端午节,竞赛还没真实开端,湘江两岸已是人头攒动,十八总码头下的沙弯水域集合了16条大龙舟……一时刻,宽阔的江面显得有些拥堵。下午两点,十六总码头忽然来了许多身穿中山水手服装的生疏汉子——本来,十六总为确保在与老对手和平街龙舟队的竞赛中不负众望、十拿九稳,从湖南汉寿请来了参与过亚太地区世界皮划艇竞赛并获奖的专业部队来主划龙舟。
三位专业教练带着50位健壮的水手登上龙舟,陈建文坐在新买的快艇上,看着船队扮演猛龙过江,敲锣打鼓为他们助威;另一边,和平街码头也从市郊乡村选出精悍有力的队员;岸上的人们只等竞赛开端,一比高低。
战鼓咚咚作响,号角此伏彼起,竞赛开端后,十六总龙舟形同一人,打开巨臂飞速行进在激流中,没用太长时刻就把和平街码头老龙舟抛在后头。看着远去的中山队背影,和平街码头龙舟只好打道回府。大伙无声地将龙舟抬回家,有人开端盘算着来年也要集资造一条新龙舟,再招集一批专业划手一雪前耻。
不过,除了十六总和和平街码头的竞赛,当天九总和文星龙舟的“斗标”也反常生猛。下午团体游河时,文星龙舟一向找机会挨近屡次打败自己的九总龙舟,想与其进行“决战”,可九总龙舟一向逃避,局面相持了两个多小时。最终,当九总队员们专心致志看着十六总船队大胜回港、欢庆成功时,文星龙舟距自己只要几米的间隔,跟着文星队指挥一声令下发动龙舟,九总龙舟不得不在落后的状况下被逼参与竞赛,奋勇赶上,在江面上划出奔涌的浪花。
间隔结尾800米时,九总仍是落后于文星,队员们计划抛弃。不过,身材高大的副指挥不甘心,跳起来自动替换现已精疲力竭的正指挥,大声呼吁为队员们加油。奇观总算呈现了,九总的龙舟再次开足马力追上来,两船齐头并进时,文星的水手看见对手追上来,就有些乱了阵脚,而九总的龙舟越划越快,总算在抵达结尾时以“一仓水”之先打败对手。
2012年4月,在一个雨后初霁的下午,我推开了易玉兰白叟的家门,当我阐明来意问起湘潭老街龙舟前史时,白叟说起了深藏心底的龙舟往事。
易玉兰白叟很早就失去了老公,靠拉板车、卖米粉养活家里的儿女。因为精干、肯吃苦,再加上为人豪爽,30多岁时开端担任安排老汽车站码头的龙舟活动,是湘潭仅有的一位女会长。
每年龙舟活动一开端,她家就热烈起来:到杨梅洲船厂要木材、请木匠,到长沙买布疋锣鼓,到乡间找“做大桨”的老师傅……不论龙舟队短少什么,她都能想办法准备到,以至于其时老汽车站的龙舟被人们称为“玉兰”号。
2000年今后,年老体衰、只能靠低保保持日子的易玉兰再也没才能持续安排龙舟竞赛了。曾有人暗里找她购买那条年久失修的旧龙舟,被她一口拒绝。她说那是老码头人的精力,便是烂也要烂在河里,让它完璧归赵。而当年40多位水手穿的绿色服装也规整洁净地保藏在她家的阁楼上,她说:“这是老汽车站龙舟队的最终一点宝物”,希望能把它们交给新的主人。可新一代的主人在哪里呢?
2016年春天,湘潭自发成立了一支“夕阳红龙舟队”,他们都是退休白叟,想在有生之年为宏扬湘潭民间传统文明、保卫龙舟拼搏精力作些奉献。2016年5月7日,“夕阳红龙舟队”的老伙计们用1万8千元把存放在株洲的和平号龙舟拉回了湘潭,安放在湘潭大埠桥码头河堤之下。因为经费紧张,白叟们自己着手修补裂缝、抛光上漆,做好下水前的预备工作,光彩夺目的“夕阳红龙舟”大旗飘扬在湘江老码头的上空。
不过,这种安慰依然是暂时的,惋惜和担忧挥之不去。跟着老城棚户区改造的进行,老码头社区名存实亡,河街居民涣散各地;年轻人不肯参与费时、耗力又没有经济报答的竞赛活动;市郊河滨的青年人大部分外出打工可贵请回;尽管湘潭每年有一些酷爱龙舟活动的人士捐钱、出物协助筹办端午龙舟赛事,但掩盖不了短少传承根基和开展土壤的实际。